一、《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一輯》,(Z126/182,特藏阅览室)林慶彰主編,台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 2008年出版。

民国时期的经学既不走汉学或宋学的路,也不循清人所走的『清代汉学』的路。那时候,是个大变动的时代,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个传统价值观崩溃的时代。它的特色可以从本丛书所收经学专著反映出来。民国时期的经学著作约有一千种,《民国时期经学丛书》收录1912至1949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学研究专著约九百余种,预计分六至七辑影印原版出版,每辑预出六十册。此次出版第一辑,收书一百余种,全部影印成十六开本,精装六十册。内容包括呂思勉《經子解題》、蔣伯潛《十三經概論》、曹元弼《周易鄭注箋釋》一至九、郭沫若《卷耳集》、章太炎《廣論語駢枝》等。
二、《The innovation complex :­cities, tech, and the new economy》,(F290/Z94,逸夫馆西文借阅室)Sharon Zukin著,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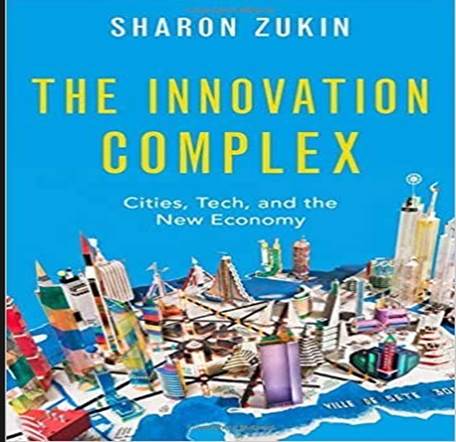
近年来,“创新”刺激了由科技产业领导的城市经济复兴。投资者们促进了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政府领导者们建造了科技中心,科技社群的“布道者”联结了年轻的软件工程师与科技巨头。他们让城市转型为一个创新综合体,一方面扩大科技产业的版图,另一方面奋力控制科技产业的权力。
在本书中,莎伦·佐金深入分析了这些创造了科技经济的人们,以及科技产业的落脚之地。通过与风险投资家、创业公司创始人和经济发展部门官员的访谈,她探索了创新之所的内涵——从编程马拉松、技术交流会、创业加速器到风投办公室、布鲁克林滨水区以及纽约的大学——新经济的规则正是由此诞生。
三、《Big data analytics in earth, atmospheric, and ocean sciences》,(P3-37/H874,逸夫馆西文借阅室)Thomas Huang等编,Wiley-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2023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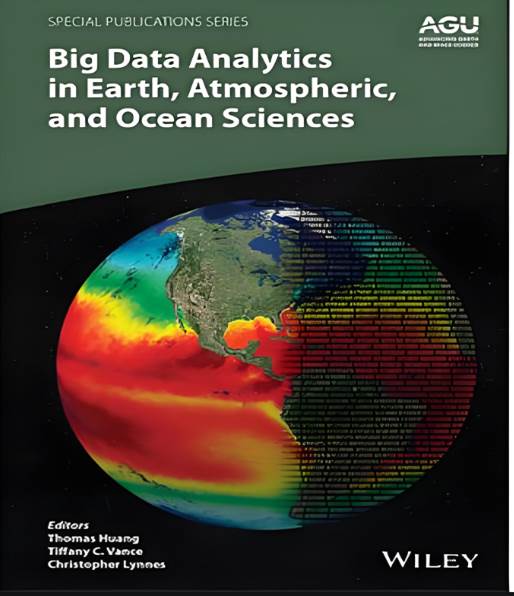
本书将数据分析工具应用于快速增长的地球数据研究,探索了分析和显示地球大数据的新方法。亮点包括:
地球大数据分析的广度介绍;为支持地球大数据分析而开发的体系结构;地球大数据的不同分析和统计方法;当前地球科学数据分析的应用程序;全面实施大数据分析面临的挑战。
四、《杨振宁的三篇学位论文》,(O4-53/19,自然科学第一借阅室)朱邦芬, 阮东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

我的三篇学位论文——《杨振宁的三篇学位论文》代序:
朱邦芬教授和阮东教授提议,编纂出版我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三篇学位论文。这三篇论文中的每一篇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都非常重要,在各种意义上都很重要。因而我认为详细介绍它们各自对我的影响,可能对研究生在其职业生涯初期有帮助。
(一)1942年学士学位论文
1938年至1942年,我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必须提交一篇论文才能获得理学学士学位。我当时选修了吴大猷教授讲授的量子理论课程,所以我去找他,请他做我的论文导师。我曾如此描述过当时的情况:
他拿出一本1936年出版的《现代物理学评论》(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让我看其中罗森塔尔(J.E. Rosenthal)和墨菲(G.M. Murphy)合写的文章。那是一篇关于群论和分子光谱的综述文章。于是我开始接触到物理学中的群论。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吴教授指引我进入这一领域,因为这对我此后成长为一名物理学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次对群论的早期接触,对于我在物理研究中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就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1957年10月,在我得知我将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天,我写信给吴教授:
在这极为令人兴奋的时刻,也需要深刻的自我反省。在1942年春天您把我引进对称性定律和群论领域,对此我要向您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情。自此之后我的大部分工作,包括宇称问题,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15年前的那个春天您给予我的启发。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心中,并且一直很想告诉您,而今天正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时机。
(二)1944年硕士学位论文
这篇论文是在王竹溪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它由两篇关于合金比热的论文组成,使用了当时常用的近似方法,其主要思想现在称之为“平均场理论”。这两篇论文在该领域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它们确实从两个重要方面引我进入统计力学。
他的《统计力学基本原理》之美犹如一首纯粹的诗篇。统计力学成为我一生两个最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我至今仍记得,1945年的一天,王教授兴奋地告诉我,昂萨格(Onsager)在伊辛(Ising)模型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突破。在昆明而后在芝加哥(1947年),我曾试图进一步理解这一突破,但都没有成功。最终在1949年,在一次乘坐公交车时,我从卢廷格(Luttinger)那里获知考夫曼(Kaufman)和昂萨格(Onsager)的一篇新论文。这使我对统计力学产生了终身的兴趣。
(三)1948年博士学位论文
1946年一月到九月,我与泰勒(Teller)教授一起工作,非常密切。他约有6、7名研究生,每一两周他会与我们共进午餐,讨论我们的研究。他还让我给他学生的作业打分。所以我有足够的机会观察他做物理的风格。他有很好的物理直觉,尤其是对于原子、分子和核物理中的对称性,但他缺乏耐心去填补直觉背后的逻辑步骤。例如,早在1941年他与克里奇菲尔德(Critchfield)合作的一篇论文中,就提出涉及自旋粒子的核反应的复杂性,但没有给出任何证据。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给出完整的证明。
在20世纪40年代末,低能核物理是最活跃的领域之一,特别是粒子关联效应的实验逐渐展开,例如-和-粒子之间的关联。关联效应的理论计算也有论文发表,令人惊讶的是,经过出乎意料之外的大量计算项相消后,最终结果却往往十分简单。我做了一些这样的计算,很快就悟到这些相消背后必然是核物理中的球对称性的数学结果。但要证实这一论断,就需要进行细致的数学分析。经过几周的分析,我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这就是我的博士论文的由来。
这篇论文极大地增强了我对于在理解自然规律上对称性的威力的认识。碰巧要研究新发现的“奇怪粒子”,必须首先确定它们的自旋、宇称以及其他量子数,也即它们的对称性,因此,在完成学位论文一年后,我得以发表一篇关于0介子自旋和宇称的论文。这篇论文使我出名,因为这直接与朗道(L. Landau)竞争。
需要指出,这篇关于0介子的论文大量使用了场论,而这是我在1943至1945年从马仕俊教授那里学到的,学得非常地深入。
在芝加哥,我对对称性应用的兴趣,不仅在实验相关的问题中,如我博士论文中所讨论的,而且还在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上:阐明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方程。在1947年,我试图将外尔(Weyl)的规范对称性推广到非阿贝尔群。这种努力刚开始一帆风顺,但很快就遇到了棘手的技术问题,我不得不放弃。幸运的是,我最终在1954年回到这个问题上,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和罗伯特·米尔斯(Robert Mills)一起,成功地克服了技术上的困难,并就此发表了一篇短文。这篇论文现在业已成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物理学最重要的论文之一。

